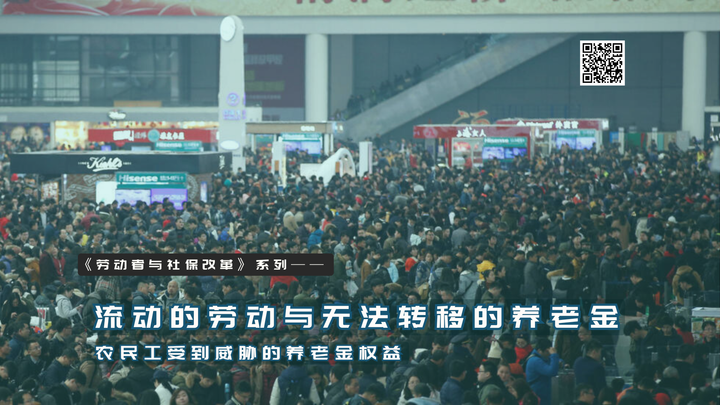【实证翻译】中国退休群体的不满与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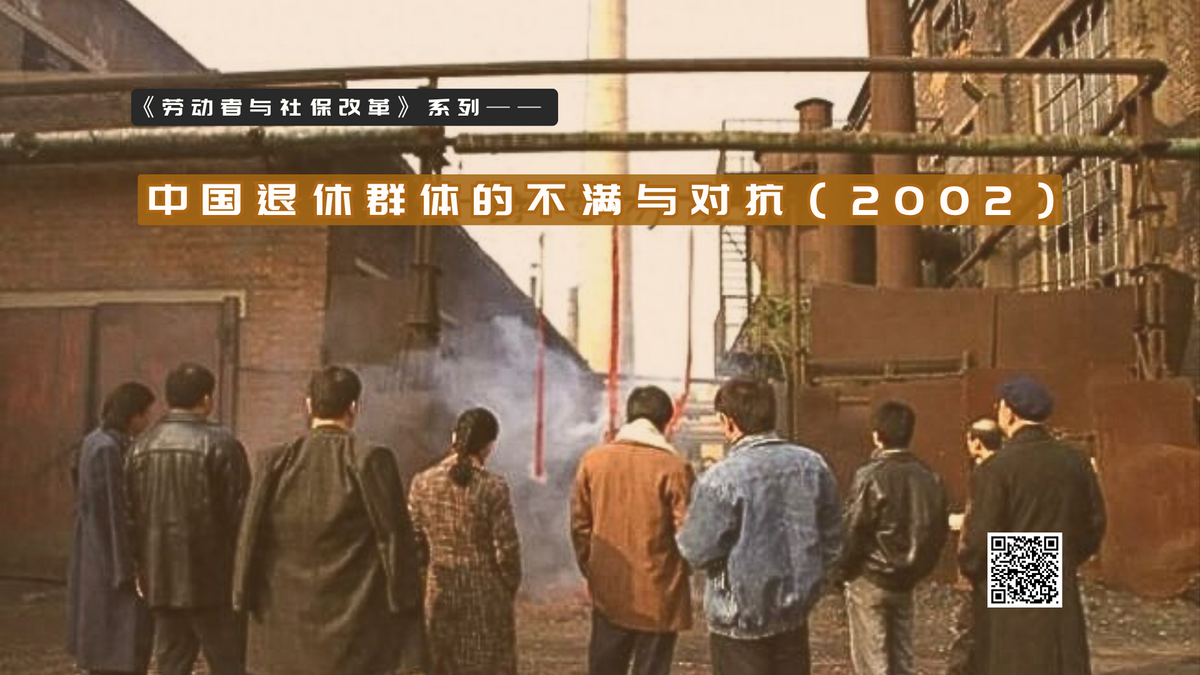
导读
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集体经济调整期间,劳资矛盾迅速攀升。不仅有声势浩大的下岗工人维权,也有因拖欠养老金而爆发的退休群体抗争。美国学者 William Hurst 通过对沈阳城市群中多位退休工人的观察与访谈,将这场“第一波”养老金静坐抗议的全貌清晰呈现。他指出,养老金不仅是退休工人的重要经济保障,更承载着国家与企业曾对他们作出的郑重承诺,这一“精神契约”正是他们坚决维权的深层动力。
大约在此后十年,在中国南方又兴起了因欠缴社会保险引发的“第二波”养老金抗争,形式虽有差异,却同样同样突显了养老问题在工人运动中的重要角色。欲了解这两波抗争的具体案例、行动动员机制及其对中国工人集体行动模式演变的深远影响,详见《从生产到再生产:中国的养老金抗议与工人集体行动的变化特征》。
关键词:社保,退休工人,下岗,国企,集体行动
译者:小凯
校对:Lope
正文
原文:China’s Contentious Pensioners
作者:William Hurst, Kevin J. O'Brien
发表:2002年
引言
近年,工人阶级的抗议活动在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城市此起彼伏。据一份工会刊物报道,仅在 1998 年,河南就发生了 247 起工人示威活动。中国无产阶级的民众行动已变得如此普遍,尤其是在工业中心地带,以至于中央领导人现在已将劳资纠纷视为对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然而,对于参与者的面貌以及抗议发生的原因,研究还很有限。一些研究者研究了下岗工人的抗争,并探讨了影响他们参与的因素。另一些研究则注意到了各种城市居民施加的民众压力,同时注意到许多抗议者的年龄往往在 40 岁以上。但是,人们对究竟是谁在助长这股抗争浪潮,以及为什么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特别容易走上街头,却知之甚少。
在近年发生劳工抗争的两个城市进行实地调研期间,养老金抗议行动显得尤为重要。本溪是辽宁的一个铁路、煤炭和钢铁工业城市,人口不到 100 万,几位下岗煤矿工人讲述了 2000 年夏天的一次示威活动,他们中一部分人参与了行动、另一部分人则是目睹了行动的爆发。示威者在市政府静坐示威,要求为此前被剥夺所有福利的下岗工人提供补贴。除了这一次以下岗工人为主体的示威外,研究者所知道的其他所有示威(超过20次)都是由退休人员发起的,目的是要求支付拖欠的养老金。
本文作者之一(William Hurst)在本溪偶然发现了两次这样的抗议活动。2000 年 11 月 25 日下午,大约 150 名退休矿工在市中心的一个主要路口阻塞了大约两个小时。他们说,他们的养老金已经几个月没有发放了,而且在11 月零度以下的严寒中,他们的暖气和其他公用设施被关闭,因为他们的工作单位无法再为他们缴费。将近一年后的 2001 年 11 月 19 日,也发生了类似的示威活动。约 100 名退休人员堵在市政府主楼门前长达数小时,他们高喊并举着标语,宣称他们的养老金已经一年多没有发放了。虽然作者无法与这两次示威者交谈,但其他几位受访者,包括一位在大型国有企业 (SOE) 担任经理的人和一位来自市政府的人都证实,因拖欠养老金和养老金不足额而举行的抗议在本溪“司空见惯”。
在山西拥有 200 万人口的矿业和国防工业城市大同,包括当地公安局官员在内的两名市政官员指出,该市近来相对平静。但他们都承认,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一些工人阶级示威活动。他们说,所有这些都是退休工人在当地政府办公室静坐示威,要求领取养老金,而没有发生过下岗工人或在职工人的民众示威。
如果来自本溪和大同的证言具有代表性,那么未支付的养老金在许多城市无产阶级成员的心目中看來占有特殊的地位。然而尚未言明的是,这种不满为何如此强烈?
养老金为何引发抗议?权利与依赖性
与本溪和大同的 18 名工人和前工人,以及重庆、上海和北京的 12 名工人的访谈表明,养老金抗议之所以如此普遍有几个原因。工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养老金视为比拖欠工资、或下岗福利更合理的不满。例如,一位本溪煤矿工人已经失业十年。在此期间,她没有从原单位或国家领取过任何款项,既没有工资,也没有下岗津贴,而且还失去了曾经享有的任何医疗保险。但她说,她绝不会考虑通过示威来获得她应得的下岗福利。相反,只有在达到退休年龄后,她的养老金被延迟或扣发时,她才会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她会毫不犹豫地坚决争取。本溪的一位技工也说了类似的话。尽管他在下岗后成功地开了一家建筑公司,并攒下了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但他声称,如果养老金被扣留或延迟,他将提出抗议或“不惜一切代价”来争取养老金。
这些言论的背后,隐含一种认为养老金优先于大多数其他权利的信念,因为养老金是国家和企业对员工多年奉献的认可,也是对那些年老无法工作的人的重要支持。本溪煤矿工人的情况显然就是如此,对她来说,强迫老人自己养活自己,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可接受的。她认为,50 岁以上的老人有不必劳动的权利。看來,这种执着源于更基本的信念:养老金是国家、企业和工人之间社会契约的基础。
工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奉献了毕生精力,以换取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和老年时体面的生活水平。虽然他们在工作期间工作时间长、工资低,但起码退休后的健康和生活得到了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支付工资或没有“下岗”福利可以被视为企业的又一次临时牺牲(就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大量无偿加班或下乡义务劳动一样),但不支付养老金则构成了对社会契约的根本性背弃。1992 年,重庆针织厂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被削减了三分之二甚至更多,他们用精练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总结道:养老金是过去几十年的劳动积累,是个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公司的义务可以延迟,但最终还是要履行。
这种想法在与本溪和大同其他下岗职工和在职职工的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除三人外,其他人都认为他们在退休后仍有养老金保障。他们中很少有人参加过任何索要下岗补助金或拖欠工资的行动,但每个人都强调,如果养老金不能及时足额发放,他们会认真考虑举行抗议活动。对这些工人来说,只有在退休时不支付养老金,才能表明公司已经无可挽回地背弃了雇佣协议。
三位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养老金没有得到保证,他们还说,如果他们得不到某种退休福利,他们准备上街抗议。其中一位受访者强调,由于他的子女都已下岗,一旦他不能再从事他失业十年来所依赖的零工(如扫大街和铲雪),他就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生活,更不用说保证家人的生活了。
在许多情况下,退休人员除了养老金之外别无其他生活来源。因此,与较年轻的工人相比,他们的生活更受单位左右。对年轻工人来说,兼职、打零工或找到一个新的长期职位仍然是可行的。年龄较大、有时身体虚弱的退休人员根本无法重返工作岗位。此外,即使他们设法找到了工作,老年人赚取可观收入的机会也很少。走访本溪的一家职业介绍中心后发现,所有的招聘信息都仅限于 40 岁以下的求职者,或者要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下岗工人通常从事的零散工作也往往需要体力(装卸建筑材料和散装货物、铲雪、用镐和铲子在人行道和道路上破冰等),在本溪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招工的雇主显然希望找到最年轻、最强壮的工人。至少在本溪和大同,许多退休人员(大多为男性)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就是自行车或摩托车出租车司机和自行车修理摊经营者。在许多城市,前者是一种受到管制的职业;后者看来每天无法赚到几元钱以上。
正如一位辽宁的前建筑工头所言,这些地方的退休人员无法依靠子女供养,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子女已经下岗或没有固定工资。虽然有些退休人员自己确实会打零工,这也能提供一些现金,但他们时常需要巨额医疗费用,子女不一定能负担。除一受访者外,所有打零工的受访者都表示,他们每月最多能挣几百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没有什么余钱来供养年迈的父母。
事实上,在本溪等经济不景气的城市,下岗工人向退休父母寻求支持和再培训费用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一名下岗煤矿工人依靠父亲微薄的退休金向一家出租车公司支付了 750 元押金,该公司在他失业 12 年后终于同意接收他。下岗后代的问题引起了中国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2000 年,一份面向老年人的杂志详细介绍了一个大家庭的困境,在这个大家庭中,即使是享有养老金保障的退休干部,也无法得到子女的照顾。那么没有稳定养老金(或根本没有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在向下岗子女求助时,处境只会更糟。
工人将养老金视为终极权利,而退休人员则严重依赖其工作单位的财政支付,这表明,与其他许多不满情绪相比,对养老金的不满情绪被认为更加合理,也更加强烈。
个人生活史因素
对于带着年幼孩子的 30 岁工人来说,被逮捕、殴打或以其他方式受到制裁或无法工作的可能性,要比许多带着成年子女的 60 岁退休人员更加令人生畏。正如辽宁的一位年轻示威者所解释的那样,当警方似乎有可能对一系列大规模示威活动采取应对措施时,他说:“年轻人不敢再去了,因为害怕镇压。他们有父母和孩子要照顾......年长的工人则不怕。他们认为饿死和被打死没什么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受访者表示,如果他们的养老金没有发放,他们愿意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都是文革期间及其刚结束时的激进活动人士和青年领袖。换句话说,今天许多争取养老金的老人就是昨天的红卫兵。
回望灿烂的过去
退休人员也倾向于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例如,本溪和大同的几位退休人员甚至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更好,他们愿意回到那个时代,放弃改革带来的任何成果。作为在国家社会主义鼎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今天那些积极抗争的退休者的动力部分来自于对他们年轻时的安全感和对自由的憧憬。
如今的退休人员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对当今这些陷入困境的工业巨头的衰败往往怀有愤懑之情。尽管他们像怀缅过去的农民一样,可能低估了过去的负面影响,反而理想化了一个物质进步、政治参与空前的美好时代。尽管他们的这种情感部分来源于对“毛主义”的理想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情绪就没有现实意义。关于光辉过去的神话,和真实历史一样,都具有激励人心的力量。对一些退休人员来说,那确实是一个辉煌的年代。对许多国有企业的工人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期,激进主义受到鼓励,个人自主性较高,工人一度在车间层面对管理层拥有真正的话语权。
即使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几年里,中国工人仍然保持着崇高的地位。在本溪的两位老厂长的记忆中,三中全会(1978 年)前的那段时间是车间空前和谐、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主要是因为华国锋(和其他一些人)发起了一项惠及国有企业的重大投资计划。即使在改革开始后很长时间里,养老金仍然是国有企业长期工人的一项重要特权;养老金将无产者与农村大众区分开来,承诺提早退休并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减少对家庭的依赖,提高个人自主性。
无论是神话还是现实,无论是过去的经历、破灭的期望、朦胧的记忆还是对昨日胜利的理想化看法,所有这些感受加在一起,足以让工人对目前的边缘化、贫困和无能为力产生怨恨,并对城市无产阶级受到尊重、其成员从摇篮到坟墓都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日子产生向往之心。
退休人员的抗议是道德经济上的反抗
一位时有遇到养老金不足额发放的退休人员曾这样表达自己的不满:“国家现在已经不尊重我了,连最基本的承诺都不愿意兑现。”这一情绪的深度,在一次采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位国企高管抱怨,大批退休人员不断缠着他要养老金。他说,这些人根本不理解市场改革的基本逻辑,依旧固守着企业理应满足其一切需求的过时观念。一位市政府官员也指出,退休人员普遍拒绝接受以市场为导向的削减政策,执着于过往企业与职工之间“应有关系”的旧观念。而一位下岗后创业的前干部则更为直接地表示,他的老同事和新雇员(主要是下岗的国企工人)都需要经历一段“思想改造”,以摆脱过去那种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
除了一些管理人员和干部之外,几乎所有工人阶级受访者都对市场改革公开表示敌意,声称他们和国家在改革开始之前过得更好,并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希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社会秩序。一些受访者甚至认为,中国社会正开始向 1949 年前的腐败、贫困时期靠拢,而且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走腐败加剧、不平等扩大的下坡路。例如,本溪的一位受访者在长篇大论地讲述“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好”的原因时,最后感叹道:“铁饭碗比空饭碗好得多。” 另一位失去医保的重庆退休人员用一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普遍的侵犯感和愤怒:
我为建设单位、加强军队、保卫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工作了一辈子。这些年来,我每天工作 15 个小时,从来没有休过假,也没有要求过加班费。现在我老了,工厂至少应该保证我的健康。单位给不了钱,国家也应该想办法。现在单位和国家怎么能不管我呢?这一点也不公平!尤其是厂长还拿着 15 万元的年薪。如果毛主席还在,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虽然很少有受访者寻求全面复兴毛泽东思想,但许多人确实希望重振互惠和自给自足伦理,将其作为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
结论
中国的养老金领取者也很容易参与抗议活动,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履历。他们从许多养家糊口的要求中解脱出来,特别有可能发起抗议活动,为自己申冤。许多退休工人的行为也是出于一种怀缅感。许多 年长的工人都是在工人受到尊重、生计得到保护的时代开始职业生涯的,他们渴望回到受到国家尊重和照顾的时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刚刚结束时,许多退休人员都已步入而立之年,因此他们的个人历史也与文化大革命有关。这也很可能对他们今天的争论起到鼓励作用。
最后,中国退休人员的抗议活动显示了道德经济反抗的因素。这也提醒我们,许多退休人员的激进主义主要基于生存诉求和主客关系被切断的感觉,同时帮助我们跨越时空,将有争议的中国老年人与其他地方的老年激进分子进行比较。
中国劳动趋势发布文章均欢迎转载!请记得说明来源,感谢!
如果你也对于数据新闻、实证资料或文献翻译有兴趣,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为理解当代中国劳动议题、工人处境贡献一份力!欢迎直接寄信到我们的邮箱: [email protected] 你可以在信件中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谈谈你熟悉的劳动议题或相关的实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