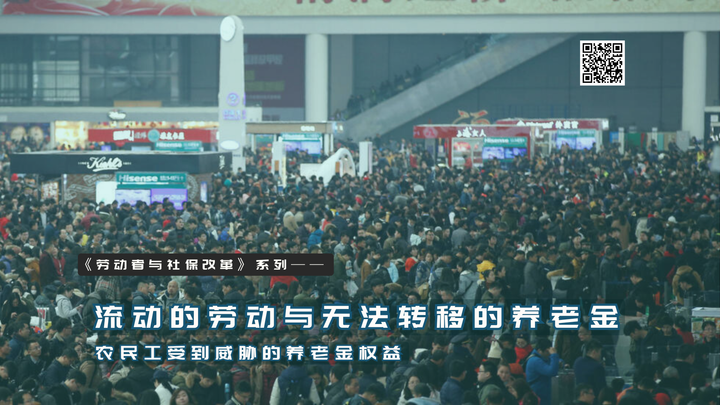【实证翻译】中国农民工的照护负担

导读
在医疗和养老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中国的养老系统高度依赖非正式照顾,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非正式照护的责任主要由子女承担。即使老人住院,由于医护从业者的缺乏,仍需要子女承担一定程度的辅助照护工作,这对他们造成很大的负担。在孝道文化的影响下,非正式照护者往往需要承受多重压力。
关键词:养老,农民工,医疗,子女,孝道文化
译者:Zen
校对:石器
正文
原文:The Care Burden of Chinese Migrant Peasant Workers
作者:Longtao He
发表:2021 年
引言
“照顾自己的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人就得孝顺。”(第一位受访者:女儿,41–50岁,再婚,父亲患病)
“我们这一代、我父母那一代以及再上一代,践行孝道的方式几乎是一样的。然而,我孩子这一代可能就不会一样了。如今的中国,金钱几乎凌驾于一切之上,包括道德。孝顺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第一位受访者:女儿,31–40岁,已婚,父亲患病)
上述评论来自两位农民工,她们的父亲在几个月前分别被诊断患有癌症。第一位受访者的评论反映出在中国,照顾父母与“孝道”之间密切且重叠的关系。孝道是中国的一种文化规范,要求子女对父母履行照护、尊重与服从的义务(关于21世纪的孝道讨论,参见Terry等,2016)。在所有儒家文化社会中,孝道是规范家庭关系最为深远的价值观之一。它调节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促进代际之间的互动,并增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力(Chan等,2012)。
根据第一位受访者的说法,照顾父母是尽孝的一种方式,而孝道是人必须履行的责任。第二位受访者的评论则反映了中国社保福利制度的现况。相较于一些西方国家,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年福利制度尚未发展完善。在第二位受访者看来,孝道是延续了几百年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但她认为,下一代可能不会像上一代那样尽孝。在她的解释中,消费主义的兴起与对金钱的崇拜是孝道衰落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可能体现出对过往的理想化怀旧情感,以及对当前孝道实践与观念转变所带来后果的担忧。
本书旨在探索中国农民工(如前述两位参与者)是如何理解并看待照顾患病父母的经验。正如第一位受访者所指出,孝道是中国人作为“人”的一种基本责任,因而可以预期,它在个体理解其照护行为、经验与感受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笔者采用了话语分析的视角,以探究围绕孝道照护所形成的话语机制与内涵,尤其关注这些话语如何塑造了参与者的照护经验。在快速变化的中国,传统价值与实践正受到急剧城市化、全球化与公共教育普及等背景变迁的强烈冲击(Lin, 2013;Rofel, 2007;Wang, 2016)。人们担忧后代不再尽孝,这种情绪不仅存在于老年照护者之间,也引发了政策制定者与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试图理解当前孝道的社会建构方式,以及多种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如何在近期与未来长期内影响这一构念。
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历了重大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革,这些变革加剧了老年癌症患者的照护需求,并同时加重了成年子女的照护负担。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即那些从农村地区迁徙至沿海或其他经济发达城市、并频繁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劳动者。他们多从事蓝领工厂岗位或小型私营企业的基层职位,始终处于流动与临时性的状态。当代中国社会中非正式照护行为与孝道实践正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而农民工群体中尤为如此。本章将重点探讨这些社会经济变迁如何可能影响农民工的照护负担。
老年癌症患者日益增长的照护需求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极其迅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以及各类癌症发病率的持续上升(Chen, 2009;Chen等,2016)。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老年癌症患者照护需求的显著增加。经过近30年的经济改革与快速增长,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两个显著趋势:一是人口显著老龄化,二是生育率持续下降(Zhang等,2012)。根据Yi与George(2010)以及Zeng等人(2013)的数据,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1950年的41岁增长至2005年的73岁。Zeng等(2013)预测,到2050年,男女平均寿命将达到84.8岁。与此同时,生育率也出现了断崖式下降,从20世纪50年代每位妇女平均生育超过6个孩子,下降至2005年的1.6至1.8(Zeng等,2013)。
许多学者认为,家庭规模的缩小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成功(Hesketh等,2005;Wang等,2005)。该政策自1979年起实施,规定每对已婚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Hesketh等,2005)。部分学者(例如Cai,2010)认为该政策并非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另一些学者(如Feng等,2013)则指出,城市化、对饥荒的恐惧(1959–1961年)、“大跃进”所带来的社会变革、195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以及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迁也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如此,他们仍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更替水平指平均每名妇女大约生育2.1个孩子,意味着出生和死亡人数趋于平衡——译注)。生育率下降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如个人主义日益盛行、女性权利的提升、离婚率上升等。从微观经济理论角度来看,在当代中国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也是一个关键因素(Wang等,2011)。根据Gallagher-Thompson等人(2012)的数据,200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6.7%;即使在高死亡率假设下,预计到2050年,这一年龄段将占总人口的24%以上。
尽管年龄的增长是一个复杂现象,取决于基因、行为与生理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且寿命延长的影响难以预测,但研究已普遍确认,个体年龄增长与健康问题频发之间存在明确联系(Zimmer,2016)。Tang等(2013)指出,近年来中国癌症发病率显著上升,并已成为全国范围内的首要死亡原因。Chen等(2016)指出,中国癌症的主要特点在于:肺癌已成为癌症死亡的首因,其次为食管癌、胃癌与肝癌;农村居民在所有癌症类型上的死亡率普遍高于城市居民。
中国近年来癌症发病率的上升(Liu,2004)可归因于多种因素,例如人口老龄化、工业污染与营养不良(Blot等,1993;Gong等,2012;Xu等,1989)。这一趋势加剧了对提高老年癌症患者照护服务的迫切需求,也凸显了在患者临终阶段保障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性(Phillips等,2010)。
非正式照护
人口老龄化与癌症发病率的双重上升,不仅引发了对老年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关注,也加重了照护者的照护负担及其健康状况问题。在近年来临终关怀研究中,学者们开始认识到非正式照护是实现重病患者福祉的整体方案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Cohen & Deliens, 2012)。大多数严重疾病患者个人无法独立照顾自己,而是依赖于家庭、朋友及社区提供的支持(Papastavrou等,2009)。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姑息治疗是一种是一种提高身患危及生命疾病患者及其家庭生活质量的照护方式。”(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d.-a,第1段)。推动姑息治疗的政策不仅着眼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也重视家庭成员的需求,因为他们往往承担着主要照护者的角色(Cohen等,2015)。Applebaum与Breitbart(2013)指出,全面的姑息照护不仅要回应患者的需要,也要顾及其非正式照护者,既保证照护的效率,也要保证其效果,从而提升患者的生命质量。
Hooyman与Kiyak(2008)指出,许多研究并未清晰界定“非正式照护者”的含义。根据一项对2000年至2011年间,主要在英国和美国发表的非正式照护文献的回顾性研究显示,56%的文章未对该术语进行明确定义,12%的研究则将其限缩为仅包括配偶或子女等家庭成员(Aoun等,2013)。Palm(2013)提出更广义的定义,认为非正式照护者包括所有未被正式雇佣的非医疗人员。基于此定义,非正式照护者可涵盖家庭成员、亲戚、朋友、邻居及志愿照护者,他们提供生活协助、情感支持、医疗帮助、经济资助等服务。虽然非正式照护常被等同于“家庭照护”,但实际上其覆盖范围更广(Hooyman & Kiyak, 2008)。
在Lin等人(2020)所列出的所有非正式照护者类型中,成年子女在满足年长父母需求时,承担的责任比平均值高。Palm(2013)认为,子女与父母之间是一种独特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朋友关系或伴侣关系,其内在价值更高。除了配偶外,生病的父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年子女,因为子女处于满足其需求的独特位置(Li等,2019)。在中国语境中,成年子女基于“孝道”的伦理责任,被寄予照护与支持父母的特殊道德期待。虽然非正式照护者可能还包括其他家庭成员与朋友,但在本研究中,笔者将非正式照护者限定为成年子女与儿媳(考虑到在传统中国,儿媳在照护中的重要角色;参见Palm,2013)。
根据Pizzo等(2015),非正式照护者兼具照护协调者与服务提供者的双重角色,对患者的福祉影响很大。Palm(2013)指出,由子女照护的年迈父母更有可能接触到正式照护资源,因为子女往往会协助其申请正式照护服务。非正式照护者的照护负担受患者疼痛程度与心理困扰状况影响,照护者的福祉增减与患者的生活质量呈正相关(Contro等,2002)。
此外,社会养老机构资源不足与费用高昂也提升了非正式照护者的重要性。中国已出台多项政策,致力于建立更完善的老年照护服务体系,但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以家庭照护为核心(PRWeb,2013)。中国许多城市提出了所谓“9073”养老服务模式,即“90%的老年人接受居家照护,7%接受社区照护,3%接受机构照护”(Albany, 2013,第4页)。然而,机构照护所需的基础设施尚未建立(Albany,2013)。目前,仅有1.2%的中国老年人居住于养老机构,而一些西方国家该比例高达8%(Gallagher-Thompson等,2012)。此外,中国公立养老院的入住费用已高到令大多数老年人难以负担的地步(Liu等,2019;Zhang等,2012)。
农村老年人对于其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子女能否提供照护表示愈加担忧。大多数身患重病的老年人仍选择居家疗养,这意味着他们主要依赖非正式而非机构照护(Albany,2013;Diamond,2009)。然而,近年来由于成年子女大量外出务工,农村老年人面临照护资源短缺的问题(Wu等,2008;Zhang,2019)。尽管农村地区对机构照护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国政府也在努力增加养老机构建设,但根据Zhang(2019)的估算,在可预见的未来,家庭照护仍将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照护来源。根据Shi与Hu(2020)的研究,农村居民普遍倾向于家庭照护而非机构照护。但家庭照护过于依赖子女,这也带来一个主要隐忧:无人照顾。此外,农村老年人还担心难以承受基本医疗费用与生活开销(Huang,2018)。
本研究的参与者属于中国社会中一个自1979年经济改革以来受到显著影响的人口群体。自1979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由国家主导逐步转向市场导向(Zhang & Shunfeng, 2003),这一变革显著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大量以年轻人为主的人口从农村地区涌入大城市(Chang, 1994;Zhu, 2001)。这一迁徙群体被称为“民工”或“农民工”。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农民工的父母已步入老年,仍居住在农村地区(Wang, 2016)。在本研究中,笔者旨在探讨农民工在其父母患有晚期癌症的情况下,是如何履行和实践家庭照护的。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在收入与社会地位方面通常处于不利地位(Wong等,2007)。根据Lin(2013)的研究,公众普遍认为农民工“不够现代化”,缺乏进步性。Lin(2013)进一步指出,男性农民工常通过“孝道”来建构自我认同,以便在陌生且充满不平等的大城市工作环境中理解自己与身份的意义。然而,由于地理距离遥远及经济条件有限,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与生活的同时,要照顾身处农村、需要照护的年迈父母,面临诸多现实困难(Joseph & Phillips, 1999)。此外,在当前高度市场化的大城市中,农民工几乎不可能获得批准农村老家照顾有需要的父母,即便是申请无薪假期(Lin, 2013)。除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地位较低之外,其农村家庭在获取社会福利方面亦处于劣势。有关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进一步讨论。
农村家庭的福利制度不足
纵观中国历史,即便是最基本的福利安排,也主要根植于家庭内部的支持机制之中(Gruijters,2017)。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老年人更普遍地依赖家庭照护,而非机构照护(Jackson & Liu,2017)。尽管近年来政府开始关注养老支持体系的完善,但中国尚未建立起一个覆盖全面的老年社会保障系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Liu & Sun,2016)。福利供给的不足导致家庭往往成为晚期照护的主要,甚至是唯一资源。与此同时,医疗费用不断上涨以及慢性病模式的持续扩展,使患者及家庭照护者所面临的经济负担愈加严峻(Burns & Liu,2017)。
养老金制度
经济改革后,许多国有企业的破产与裁员导致了原有“单位制”城镇职工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问题(Liu & Sun,2016)。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则彻底摧毁了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基础(Williamson 等,2012)。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三大国家资助计划构成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第一支柱为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广泛被认为是待遇最优的社保体系,但截至2008年,仅覆盖了约5%的劳动人口(Williamson 等,2012);第二支柱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28%;第三支柱为农村居民自愿参保的养老金计划,仅覆盖了7%的劳动人口(Williamson 等,2012)。这三类养老金制度之间存在极大差距(Salditt 等,2007),其中第一支柱为参保人提供最优待遇(Salditt 等,2007)。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最后一类——农村养老金计划。
据Liu与Sun(2016)称,中国政府一直在尝试扩大覆盖范围并缩小三类制度之间的差距。2009年,中国在部分县区试点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Gao 等,2012),并逐步推广。该制度包含两个层次:(1)自愿缴费型个人账户;(2)非缴费型基础养老金(Williamson 等,2017)。若成年子女自愿参保,父母双方可无须参保便获得每月70元的基础养老金(Williamson 等,2017)。在缴费型层级中,参保人每年可选择缴纳100元至2000元,且连续缴满15年以上。根据Ma H.(2015)数据,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四川农村年均收入约为7000元。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男性60岁,女性55岁),可领取与缴费额相对应的养老金(Williamson 等,2017)。
2008年前,全国仅存在一些小规模养老金计划,覆盖面仅达10%的农村居民(Williamson 等,2017)。根据同一研究,到2014年底,大部分达到年龄门槛的农村居民已符合加入新农保的资格。此后,该制度扩展至城镇失业人员及家庭主妇等城市社会群体(Gao 等,2012)。Williamson 等(2017)认为,得益于政府的推动,城乡养老保险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例如,2014年政府取消了对公务员的全额财政供养养老金制度(Liu & Sun,2016),使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相应下降。
不过,Liu与Sun(2016)指出,有关农村养老保险“扩展显著”的说法被夸大了。他们进一步指出,该制度提供的平均养老金(每月80元)远远不足以支付基本生活开支。举例而言,根据Williamson 等(2012),2012年1公斤猪肉的市场价已超过30元。此外,尽管符合参保资格,农村居民——尤其是在城市务工的年轻人——普遍不愿加入该制度(Liu & Sun,2016)。笔者所调查的24位参与者中,仅有4人参保(其中1人参加的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所有参与者的父母均未加入该制度的自愿缴费层级。Gao 等(2012)指出,人们对该计划的透明性与可靠性表示担忧,因为养老金账户管理缺乏公开机制,个人账户资金多数被用于支付现有参保人的待遇。因此,许多农民工选择不参与新农保计划。与此同时,尽管政府试图改善农民工在私营企业和工厂中的社会保障状况,但多数雇主仍拒绝将农民工纳入工作场所的养老保险体系(OECD,2012)。
农村的社会与医疗保险
虽然中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在实现全国覆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资金依然严重不足。自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启动以来,该制度已覆盖约8.33亿农村居民,包括农民工,占农村总人口近90%(Babiarz 等,2010)。(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生活与工作,但其户籍仍在农村,故被视为农村居民。)为了控制医保基金风险,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高自费比例设计(即患者在每次就医时需支付较大比例的费用),这使得医疗服务对农村居民而言仍难以负担(Li 等,2012)。近年来,农村医保制度已开始针对重大疾病如癌症、大病住院等提供专项保障(Blumenthal & Hsiao,2015;社会保障官网,2017)。据官方数据(2017),胃癌、食管癌、结肠癌和直肠癌等多种癌症的报销比例在部分地区已高达80%。
尽管如此,农村参保家庭的自付费用仍然过高(Xing,2015)。对于患有慢性病的患者,其长期照护费用并不在医保覆盖范围内(Xing,2015)。门诊服务、康复治疗、常用基础药品与临终关怀(缓解末期病患疼痛、实现其生命终期愿望的照护)未被优先保障(Li 等,2012)。笔者所开展田野调查的四川省阆中市在新农合制度基础上推出了一项重大疾病社会保险政策,用以救助罹患胃癌、食管癌等重病患者(即笔者研究中参与者父母最常见的癌种)。该政策最高可报销住院费用的75%至80%,但诸如部分必要药品、营养液、陪护床位费、门诊服务等则保障报销比例较少甚至完全未覆盖(Zhang 等,2010)。
其他政府支持政策
新农保制度允许子女为父母购买参保资格,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被视为政府对照护者及其家庭的一种支持。这一安排也进一步强化了家庭成员之间彼此负责的道德观念。然而,正如上文所述,该制度的覆盖范围极其有限,因此对照护者的支持也十分有限。
政府亦尝试通过其他方式鼓励家庭照护,例如通过继承法给予履行孝道义务的子女以优先继承权(Chou,2011)。然而,对于许多农村家庭而言,继承权的承诺不足以激励子女达成照护协议(Chou,2011)。此外,农村老年人在生命晚期往往无法为子女留下可观的财产(Mao,2010)。现行法律也未明确规定父母应如何在子女间分配财产,亦缺乏衡量孝道履行程度的具体标准(Palm,2013)。在独生子女家庭中,该法律的激励机制更是无效,因为无论是否尽孝,子女终将独自继承全部家产。
在一些城市,如北京和上海,个别慈善组织或地方政府对罹患重病(如癌症)的老年人提供小额津贴等支持,并对其家庭成员提供家庭照护技能培训(Hu 等,2020;Mao,2010)。然而,总体而言,政府对非正式照护者的支持仍极其匮乏(He & van Heugten,2020;Mao,2010)。对于此类支持的需求在国际范围内亦为长期性问题,例如Barusch(1995)曾指出,许多国家因政府缺位而严重削弱了家庭照护者对老年人照护的投入。
非正式照护者的照护负担
现有文献日益重视非正式照护者在照护亲人过程中所承受的多重负担(Seo & Park,2019;Xiao 等,2014)。本节将简要介绍非正式照护者所面临的财务负担、身心压力以及文化与哲学层面的压力。
养老金与医疗保险政策的不足导致患者及非正式照护者(主要是成年子女)必须共同面对严峻的经济困境(Jung & Liu Streeter,2015)。在过去30年中,中国人均自付医疗费用急剧上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发布的中国医疗体系评估报告,自2005年至2012年间,中国总体医疗支出呈快速增长趋势。尽管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但私人支出与自费比例亦达到最高点(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5)。
尽管没有确切数据说明家庭照护者承担了多大比例的自费医疗支出,以上数据已足以反映家庭层面的财务压力。即便在新农合及其配套的大病保障政策下,中国人中仍流行一句俗语:“辛辛苦苦三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Xing,2015,第14页)。
根据Lu 等(2010)关于中国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的研究数据,66.8%的照护者为照护亲人而做出重大生活调整或辞职,55%的家庭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68%的家庭将大部分积蓄用于治疗和相关开支。此外,非正式照护者常被称为“隐形劳动力”,他们的劳动往往不被报酬也缺乏支持(Meier,2012)。Meng(2013)指出,男性毎周每提供10小时护理,带薪工作时间平均减少48分钟,而女性平均减少35分钟。
在中国,医院通常不提供充分的床旁护理。除注射与输液由护士完成外,其余护理工作通常由家属承担(Pan & Feng,2007)。这意味着至少需一名家庭成员留守医院,为患者进行喂食、洗漱等日常照护。Xu 等(2016)指出,中国医院的护士与床位比例远低于西方国家。Wang 等(2014)研究发现,护士配置比中的缺勤情况常被忽略,导致真实护理人力不足的情况比研究数据显示的更为严重。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亲眼看到护士的工作繁重,在一个约45张病床的病区,常仅有五至六名护士,几乎没有时间处理除注射与输液之外的病患照护任务(她们还需协助医生及处理行政事务)。最终,包括输液监控、仪器数据观察、喂饭、如厕协助、入院文件、洗澡等任务,皆需由家属承担。完成这些护理任务常常要求照护者放弃部分甚至全部有薪工作时间;而在当前制度下,他们往往连无薪假也难以申请(Ye 等,2013)。收入的流失进一步加重了非正式照护者的经济压力。
为了协助年迈亲人善终,家庭照护者往往不仅在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同时也承受严重的身体与情绪压力(Lu 等,2010)。照护者常经历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社交隔离、经济紧张和生活质量下降等负面影响(Ugalde 等,2012),且普遍健康状况低于非照护者(Rehman 等,2009)。首先,研究表明,照护者经常表达对自身健康的担忧,例如极度疲惫、失眠或睡眠中断(Aoun 等,2013;Rehman 等,2009),他们往往因缺乏时间而无法照顾自己。其次,照护临终父母的同时,还需维持自身生活质量、重塑社会角色与人际关系、处理情绪冲突等,使照护者的自我认同与社会互动变得复杂化(Ugalde 等,2012)。上述因素可能危及照护者的心理社会健康,诱发诸如抑郁、焦虑、人际关系丧失等问题(Aoun 等,2013)。
根据Liu 等(2015)研究,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大多数中国农民工更易罹患各类慢性病,其健康状况普遍劣于其他人口群体。Mao(2010)也指出,年长或健康状况不佳的非正式照护者往往承受更沉重的照护负担与压力。作为子女,他们也可能同时面临来自配偶、父母、甚至祖父母等多重角色的冲突(Mao,2010)。
对许多晚期癌症患者而言,死亡在中期内是医学上几乎不可避免的事实。但谈论死亡在实践中却极为困难(Kortes-Miller,2015)。即使在西方临终照护领域,专业人士也常难以与患者进行坦诚的死亡对话,尽管向患者公开其临终状态已成为惯例(Kortes-Miller,2015;Tse 等,2003)。专业人员通常会评估患者的症状与需求,探询其意愿,并尽力促使患者参与未来规划的决策过程(Kortes-Miller,2015)。
然而,在中国,医生与护士很少与临终患者谈论死亡(Fang 等,2009;Kendall,2006)。事实上,患者的真实病情通常并不会向其本人披露(Jiang 等,2007)。如需手术,医生往往要求成年子女或配偶签署同意书,而非由患者本人决定(Cong,2004;Hancock 等,2007)。对父母隐瞒病情的做法,使家庭照护者可能陷入情绪困扰与孤立感之中(Aoun 等,2015;Tse 等,2003)。不告知病情剥夺了家属完成“心理终结”的机会,例如道歉、感恩或告别等。此外,这种“隐瞒”行为也与孝道文化相关:在传统孝道话语中,与父母谈论死亡被视为禁忌(Yick & Gupta,2002)。
孝道观念也可能妨碍老年人福利制度的建立。在一些西方国家,非正式照护者的贡献已逐步受到政策制定者的认可(Corden & Hirst,2011)。例如,英国政府向家庭照护者提供小额津贴与养老金;新西兰卫生部2013年起推行政策,允许残障人士向家庭成员支付照护服务费用(Disability Support Services,2018)。但在中国,由于根深蒂固的孝道观念——其假设对年迈重病父母的照护应完全由家庭承担而非国家——家庭成员通常自行承担全部照护责任(Gallagher-Thompson 等,2012)。在笔者研究中,多数家庭照护者(即成年子女)很少寻求外部帮助,这正是孝道与家庭价值观强烈内化的体现(Gallagher-Thompson 等,2012)。
综上所述,孝道可被视为成年子女作为照护者所承受的一种文化与哲学上的“负担”。然而,Patterson 等(1998)指出,照护责任未必一定会削弱子女的生活质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生活质量是“个体在其所处文化与价值体系中,基于其目标、期望、标准与关切,对其生活状态的主观感知”(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n.d.-b,第2段)。在中国语境中,履行孝道责任的机会可带来精神上的慰藉与完整感。然而,Patterson 等亦指出,孝道话语可能压抑照护者对压力与负面情绪的表达,从而反过来损害其生活质量。无论如何,许多学者如Xiao 等(2014)与Ikels(2004)均认为,孝道很可能是中国人照护年迈父母的重要激励与动因。
照护实践的衰退与政府应对
在当前社会背景与多重照护负担的共同作用下,非正式照护者,尤其是农民工,面临着持续为父母提供照护的诸多困难。父母常常被“留守”在农村,而他们尤其在生病时迫切需要子女的照护。然而,距离障碍、假期制度、经济资源等因素的限制,使得农民工难以为父母提供有效照护。研究显示,农民工对子女的照护行为已呈下降趋势(参见 Ikels,2004;Koshy,2013;Nylan,1996;Poškaitė,2014;Wang,2016;Xu,2012)。
为应对这一现象,中国政府于2013年7月出台法律,赋予父母因子女“未定期探望”而提起诉讼的权利,此举旨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的核心价值——即要求子女照顾、尊敬与服从父母(Hatton,2013)。该法律被广泛视为对成年子女照护行为衰退的“自上而下”回应。面对这一衰退趋势,政府与社会公众近年来均表现出重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倾向,其中“孝道”成为该复兴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Billioud & Thoraval,2007;Guan,2005;Song,2015)。
小结
农民工群体因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新自由主义语境变迁的深远影响,已被广泛认定为最为显著受影响的社会群体之一,因此成为本研究聚焦探讨的适宜对象。由于该群体所处的特殊社会地位,研究识别并解释了他们所承受的多重照护负担,这些负担可能受到中国社会语境因素的加剧,也可能独立存在。
在下一章中,笔者将进一步阐述“孝道”这一核心概念,并结合本研究对象的实际语境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劳动趋势发布文章均欢迎转载!请记得说明来源,感谢!
如果你也对于数据新闻、实证资料或文献翻译有兴趣,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为理解当代中国劳动议题、工人处境贡献一份力!欢迎直接寄信到我们的邮箱: [email protected] 你可以在信件中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谈谈你熟悉的劳动议题或相关的实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