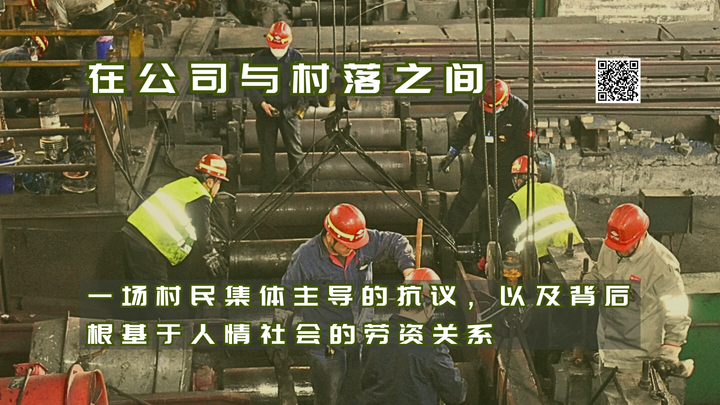【实证翻译】21世纪社会政策改革:扩大城乡基本保障

导读
本文梳理了中国在加入WTO后,党国体制下推动的社会政策改革,重点聚焦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住房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核心制度的演变与实施效果。作者指出,尽管国家财政支出持续增加,改革在表面上实现了“基本保障”普及,但由于制度设计分割化、市场化取向明显,实际保障水平高度不均,尤其对城乡居民、非正规就业群体、女性与农民工等边缘群体明显不利。
文章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威权体制与新自由主义逻辑交织下,中国的社会政策为何未能有效缓解不平等,反而加剧了社会分层与不安全感。作为社保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对整个专题进行总结。不仅描绘当下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运行图景,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持续的制度改革与社会转型中,真正公平且可持续的保障体系应当走向何方。
关键词:社保,新自由主义,威权主义,不平等
译者:kobayashi
校对:十七
正文
原文:Neoliberalism, Authoritarian Politics and Social Policy in China
作者:Jane Duckett
发表:2020年
进入21世纪初,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随着经济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党国体制启动了一系列社会政策改革,旨在为农村居民及城市中失业者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并相应增加政府在社会领域的支出。
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比从14.4%上升至14.6%,社会保障与就业支持的支出比例由10.9%提高到12.2%,而卫生支出的比例则由4%增长至7.1%。
暗面:威权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政策改革的局限性
中国的社会政策改革原则上为所有农村居民确立了养老与医疗保险保障,同时延续了党国体制在资助“基本”保障方面对全体国民的承诺。尽管这些政策常被描述为普惠以及均等化,但由于“基本”保障的内涵尚未明确定义,其普遍性仅停留在表面,政策实际操作中却使受雇于正规部门的,城市较富裕群体享有更高水平的照护与保障。通过对政府官员保留(直至2015年才进行改革)较为慷慨的保障,同时引入由雇主与雇员共同缴费的独立制度,并进一步为无业“居民”增设政府拨款但水平低微的保障计划,这些政治上权宜之计的措施最终构成了一种分割性体系,导致保障分配极不均衡。对于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仍显不足,并且明显偏向于为公务员和城市正规部门工作人员提供服务。
以养老金为例,目前存在若干不同类型的养老金制度(Zhu and Walker, 2018):包括长期以来发放给官员的政府养老金;针对非政府正规部门从业者的城市职工养老保险;以及原本各自独立、于2014年合并后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金;此外,还有1992年农村养老金部分遗留的补充制度、为因土地被地方政府征收而给予农村居民的补偿性养老金计划,以及为8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的极为微薄的“高龄补贴”。据Zhu和Walker(2018:1417)报道,这些制度在保障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政府养老金平均每月约2500元,职工养老保险约为1800元,而居民养老金则不足前两者的十分之一,仅为每月127元,使得养老金分配的基尼系数高达0.68。各制度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同样显著,尤其在居民养老金制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医疗保险方面,情况大致相似:政府官员和正规部门员工享有比其他城市和农村居民更为优越的保障。相较之下,后者需要承担更高的缴费比例。Liu等(2016)计算发现,1993年至2006年间,政府医疗支出的40%实际上流向了仅占总人口3%的群体;尽管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这一比例近年来有所下降,但到2012年仍占总支出的25%。Brixi等(2013)的研究显示,政府对公务员的人均医疗支出为2629元,而农村居民仅为78元,城市普通居民则仅为40元。此外,医疗费用,尤其是重大或慢性疾病的治疗费用,常常使许多人陷入贫困。举例来说,Si等(2019)发现,2013年山西省城市地区中,有47%的家庭因高血压及其他疾病而不得不面对“灾难性医疗支出”,其中贫困家庭面对灾难尤为脆弱。
社会政策中保障水平的不均等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便在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现象依然存在,而社会保险政策却对经济条件较好、保障较完善的人群提供了最为丰厚的福利。由于社会保险制度将福利与缴费水平挂钩,因此收入较高者获得的待遇也更优(Zhu and Walker, 2018)。与此同时,一项2012年的调查显示,正规部门职工中有95%享有医疗保险、90%参加了养老保险,而非正规部门职工的相应比例仅为58%和47%(Jiang et al., 2018:346)。这也解释了为何尽管近期政策鼓励将登记在册的农村移民纳入城市保险体系,但他们的参保率依然较低——原因在于相比城市户籍居民,他们更难获得正式的工作(同上:348)。
同样,劳动力市场化意味着劳动者可能失业,但失业保险覆盖的劳动人口比例极低,而且该保险主要在经济条件较好、就业较为稳定的人群中惠及。失业保险与养老和医疗保险一样,均采取缴费制,仅面向城市工资制劳动者,并且更可能惠及正规就业者(Duckett and Hussain, 2008)。Gao等(2019)发现,失业保险对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可忽略不计。
21世纪的教育改革在扩大受教育人数和提高许多地区教育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使教育系统内部的不平等加剧,表现为区域间以及不同阶层在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存在明显差距(Schulte, 2018)。尽管2006年的教育改革试图免除农村学生的学费及其他杂费(继2001至2004年期间对农村学费的限制尝试之后),但该改革并未解决因地方政府投入不均导致的教育质量差异问题,也未能应对城市低收入群体在送子女上学过程中因无法承担额外费用(如文具、书籍等)而面临的困境。
改善经济适用房和充足住房供应的政策同样面临实施难题。近年来的努力包括推广共有产权住房、租赁型建房模式以及棚户区改造。正如朱亚鹏所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诸多国家普遍转向放弃社会租赁住房的背景下,中国在公共社会住房方面并未将其作为优先发展领域,“通过补贴而非直接提供住房,表明中国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有助于刺激经济发展”(Zhu, 2018:48)。迄今为止的结果是,截至2015年,中国最大城市(人口超过700万的城市)中多达60%的家庭如果没有补贴,根本无力购买或租赁住房。因此,许多居民——尤其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只能居住在城市边缘的棚户区,且缺乏自来水、电力及取暖等基本设施。
另一类问题则源自于中国在1990年代城市及21世纪初农村推行的低保制度。这一制度依据一篮子基本必需品的价格计算出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对收入低于这一水平的家庭提供现金补贴。虽然现金转移支付使这些家庭的收入达到了当地最低水平,但金额普遍微薄——仅勉强满足基本的食品和部分衣物需求。Dorothy Solinger(2017)计算显示,2006年至2015年期间,城市地区的家庭低保收入仅达到当地平均可支配收入的16%至17%(而2003年这一比例为21%)。而在实际操作中,该制度的执行远比政策文件规定得更为严格,导致满足当地低保领取条件的家庭中,能实际领取补贴的不足一半(同上:51)。此外,该制度具有明显的污名化效应,因为它仅针对最贫困群体,并要求低保申请者的经济状况在社区内公开展示(Hammond, 2019;Solinger, 1999)。
鉴于各类保障计划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供给水平存在极大差异,因此21世纪这些政策的推行在减少不平等方面成效甚微也不足为奇。Gao等(2019)通过分析2002、2007和2013年的家庭及个人收入数据发现,社会福利(涵盖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低保和住房保障以及实物福利)对城市家庭收入的贡献远高于农村家庭(2013年分别为18%对6%)。在城市与农村内部(而非城乡之间)的比较中,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其他福利的影响则微乎其微。2013年低保使城市基尼系数降低了0.002,但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并未显示出明显效应。总体来看,扣除转移支付后的收入不平等在2013年比2002年更为严重,因为在此期间扣除福利前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
与此同时,社会政策在缩小区域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以及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方面成效有限。区域差距——尤其是沿海大城市与内陆农村之间——依然十分明显。农民工群体从社会保障中获益的可能性远低于城市或农村常住居民(Gao等, 2013; Gao等, 2019; Wang等, 2016)。而性别不平等问题虽然较少被研究和讨论,但其严重性同样不容忽视。Shen等(2016:76)发现,公共医疗和养老金的转移支付在性别分配上“明显不利于女性”,而Zhu和Walker(2018:1419)则指出,女性养老金平均比男性低30%。
总体来说,中国党国体制的社会政策不仅加剧或复合了不平等现象,并进一步分割了社会群体,其市场化成分也制造了新的不安全感。同时,这些政策通过缓解对市场不安全感的反对,推动了亲市场的经济政治运作。此举既避免了在政治上难以承受的再分配(例如,为增加对贫困农民的投入而减少对公务员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支出)或大幅提高政府支出,又使中共得以在维持城市支持的同时,降低先前被忽视和边缘化群体的不满情绪。
中国劳动趋势发布文章均欢迎转载!请记得说明来源,感谢!
如果你也对于数据新闻、实证资料或文献翻译有兴趣,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为理解当代中国劳动议题、工人处境贡献一份力!欢迎直接寄信到我们的邮箱: [email protected] 你可以在信件中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谈谈你熟悉的劳动议题或相关的实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