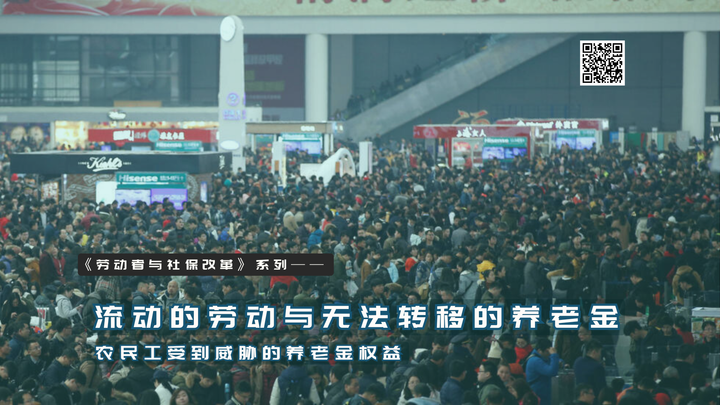【实证翻译】中国农民工的“权利觉醒”:超越代际视角

2010年代华南地区罢工潮,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疑问:自发性的罢工,或者在绝境下引起的富士康“连环跳”惨剧,是否意味着上一代农民工“任劳任怨”的形象,来到新一代已然褪色?本文作者在广东进行的问卷调查,尝试比较不同代际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以及理想的工作条件。调查结果指出,虽然新一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更了解加班和工资方面的权利,但整体仍不见得非常显着的“觉醒”。相对而言,同一时期并不乏以中老年员工为主体抗争,例如社保、经济补偿金抗争等。
当年的“新生代农民工”现在也逐渐步入中年。他们的现况是怎样,会走上与他们上一代一样的路吗?这可能是值得探索的议题。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权利觉醒,生产关系,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最低工资,工时
译者:小凯
校对:石器
专题导言
在中国,罢工从来没有被政府允许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没有行动的可能。从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到2014年裕元上万工人停工,再到近年技术行业的网络串联,工人的集体抗争以各种形式持续出现,穿过禁令、越过工会,成为这个时代不容忽视的基层声音。
本专题想探寻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为什么罢工会发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人会选择集体行动?第二,在这些行动当中,那些“外部参与者”——如NGO、学生、媒体或法律援助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说十年前的研究已经指出工资压力、社保缺失、强制加班是导致工人不满的重要原因,那么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当工人走上集体抗争这条路,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有什么样的资源与网络支撑?他们的行动如何被外界看见、理解、或被干预?
从最早提供法律服务的本地NGO,到参与维权的学生团体,再到个别地区尝试改革的基层工会,“外部参与者”既可能成为工人集体行动的帮助者,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中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近年来,随着社会空间持续收紧,一些新型抗争形式开始出现:货车司机借助微信群自发组织,程序员通过GitHub发起抗议——这些行动突破了传统组织的边界,也带来新的问题意识。
本专题希望通过对十多年间若干典型案例的梳理与讨论,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个老问题:在当代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究竟是如何可能的?而又为何总是如此困难?
正文
原文:The “Rights Awakening”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Beyond the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作者:Ivan Franceschini, Kaxton Siu, Anita Chan
发布:2016 年
(为方便阅读,本文为选译)
引言
自 2001 年学者王春光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一词以来,有关 1980 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农民工的论述不断。不过,这个词直到 2010 年才出现在政策指令中,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一号文件中强调要“采取具体措施,努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久之后,有两件事使这一代年轻工人的困境和斗争行动受到大众的关注:四月富士康(全球苹果产品的主要生产商)深圳工厂的“连环跳”自杀悲剧,以及五月本田汽车零部件工人在广东南海的罢工。前者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者则因感到不公而愤怒,进行了长达十九天的罢工,要求高于平均水平的加薪幅度和选举自己工会代表的权利。这两起事件都受到国内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导,带出一个讯息:中国的年轻农民工在困境中不会默默忍受。
以劳动标准为焦点的研究方法
为了进一步探讨上述问题,本文将重点关注一个在代际差异研究中迄今较少受到关注的因素——通过工资和工时体现出来的劳动标准。这两个方面不仅是中国农民工乃至一般劳动者最为关切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推进劳动规制改革的主要对象。因此,它们既可以作为衡量中国劳动者法律权利意识水平的重要指标,也能够为理解劳动者对理想工资与工时的认知和期待提供切入点。
工资计算系统
我们在中国的实地观察显示,计件制令工人感到困惑。中国的服装供货商工厂必须对瞬息万变的时尚风格做出反应;很多时候,工厂管理者会要求工人在同一个月内缝制不同类型的服装,每种类型需要不同的时间和技能,每种类型的计件工资也不同。然而,付款单上只显示工人在一个月内生产的总件数,而不是所缝制的各种类型的件数和工资率。因此,工人无从计算他们在生产过程中花在某种成衣上的劳动量是否准确地反映在工资上。
相比之下,计时工资制更为规范,也更便于计算。当然,管理层依然可以通过调整在特定时间单位内的劳动强度来变相影响产出,但至少工作时长本身在制度上有一定的规范。对于劳动者而言,时间工资制的一大优势在于,他们能够较为直接地将所得报酬与法定最低工资进行对比核算。这有助于防止雇主随意操控工资支付方式,也正因如此,自工业革命以来,“合理的日工作时长”与“充分的时薪标准”便一直是国际范围内劳资博弈的核心议题。
集体谈判机制、制度框架及执行机制的欠发达,加上过去三十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普遍采用计件工资制,导致中国工人不习惯以计时工资逻辑计算工资,而仅关注每月工作结束时所获工资的总额。(......) 事实上,计件工资的广泛应用,使劳动者普遍相信,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符合其个人利益。因此,在本研究所访谈的成衣工人中,绝大多数选择计件工资而非时间工资。当被问及在计件制下的超长工时时,多数工人并不认为问题出在工资制度本身,而是将其归因于个人能力与工作效率的差异。他们普遍坚信这一制度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并认同当下中国工厂普遍奉行的工作信条——“多劳多得”。
研究方法
为了验证我们的假设,我们进行了两次厂门外调查。第一次调查于 2010 年在深圳市的六家港资工厂进行。其中两家工厂各雇用约 100 名工人,两家工厂各雇用约 500 名工人,两家工厂雇用约 10,000 名工人。第二次调查于 2012 年在三家意大利企业投资的金属机械加工厂进行,它们分别雇用约 200、2000 和 7000 名工人。2010 年共回收 389 份问卷,2012 年回收 148 份。成衣厂的生产品类相当单一,金属机械厂则制造各式各样的产品,包括半导体、捕蚊器、空调零件和咖啡机。尽管产品各不相同,所有这些工厂都雇用了非熟练农民工。
这两个行业在工资支付方式上也存在差异,我们将其作为一个自变量加以考察。……因此,在将生命周期视为影响人生志向重要因素的前提下,我们将样本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年龄群体:(a) 出生于1980年之前的工人;(b) 出生于1980年至1990年之间的工人;(c) 于2000年代中期进入劳动市场的工人。在开展调查时,后一群体的部分成员只有十几岁。最年轻的一代大多仍然单身,而中间群体中里有部分人可能结婚,甚至已有子女。至于最年长的一代,其中一些人则可能已经有成年的子女,并与他们一同外出务工。
劳动时间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工作日的时长一直是工人斗争的核心问题。......表 4 显示,较高比例的金属技工认为他们目前的工作时间是合适的。在所有三个年龄组别中,有很大比例的人希望工作更长时间,这与制衣工人的情况相反(见表 3 )。平均有 55.8% 的金属技工满意目前的工时,14.5% 希望工时减少,29.7% 希望工时增加。相反,88.4% 的制衣工人希望减少工作时间。这一结果揭示了实际工时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工人对劳动时间的主观偏好。在两个行业中,年长工人比年轻工人更倾向于延长劳动时间。在这一点上,本研究的发现印证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假设,即年轻工人相较年长工人更不愿意接受超长工时。


如果月度工作时长确实是影响工人法律知识的重要因素,那么为何仍有大量制衣工人表示希望缩短工时——而且是在不了解法律限制的情况下?相反,为何在金属技工群体中,尽管有更高比例的工人能够正确指出法定最高工时,却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希望延长工时?我们推测,相较于法律知识本身,身体疲惫在其中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每天连续工作十一至十二个小时,长期以往,必然会导致身心疲劳。如果制衣工人能够明确指出法定工时上限,是否会有更多人选择八小时作为理想的工作时长?值得关注的是,几乎所有回答错误的工人对法定工时上限的估计都偏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长工时对他们而言已是常态,这使得他们倾向于认为法定工时应当更接近于自身的实际工作时长。
总括来说,尽管我们的样本数量相当有限,但我们对纺织和金属技工的实际工时和期望工时之间关系的描述性分析证实了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出的两个假设。与“第一代”外出务工人员相比,年轻工人更了解工时相关的法律权利,并且更倾向于缩短工作时长。分析结果显示,年轻工人对加班上限的规定(法定加班上限为每月 36 小时——译者注)相对更为了解,但整体认知水平依然偏低,尤其是在制衣行业(见表 6 )。数据同时表明,纺织工人超长的工作时长显著影响了他们理想工时的时数。至于金属行业工人,虽然其对劳动法的认知程度相对较高,但仍普遍希望工作时间超过法定上限。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工人均未表现出主动争取缩短工时的诉求。在这一情况下,法律知识并未转化为行动或抗争。我们认为,这与两类行业存在差异的工资支付制度密切相关。

工资计算方式与工资
在中国农民工的眼中,工作时间和工资是密切相关的。在他们看来,较短的工作时间意味着较低的报酬,而超时工作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当他们尝试计算要工作多少个小时才能赚到足够的生活费时,这就是指引他们的原则。......然而,我们的调查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年轻的工人对自己工资的期望值不仅低于年长的同事,也远远低于他们依法应得的金额。尽管样本数有限,但这一发现无疑对“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更具权利意识”的普遍假设提出了挑战。
结论
为总结与本文开篇提出的两个假设相关的研究结果,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年轻工人更希望缩短工时并享受更多生活,这一发现与“新生代农民工不愿过多‘吃苦’”的普遍观点相一致。但需要强调的是,实际上各年龄层的服装工人均处于同样的超长工时状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他们视为“懒惰”。
(2) 本研究部分印证了第二个假设,即年轻工人对自身法律权利的认知程度相对更高。受访者在加班上限方面的认知有所提升,但总体水平依然偏低,尤其是在服装行业中。至于对法定最低工资的认知,结果呈现一定的差异性。然而,本研究最值得关注的发现是,年轻工人对工资的期望不仅低于年长工人,而且远低于其依法应得的水平。
尽管不同年龄层的农民工之间确实存在某些代际差异,但诸如工资支付制度等外部因素在塑造其预期方面仍具有显著的连续性。……我们或可将这一轮新的抗议浪潮称为“中国农民工的觉醒”。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集体行动往往由已步入四十岁左右的老一代工人发起和主导。他们竭力争取的是雇主长期拖欠的社会保险缴费、遣散费与加班费,以及临近返乡前雇主依法应缴的住房公积金。这类行动并非源于对提高工资或缩短工时的诉求,而更多是出于在工厂生涯即将结束之前,再多工作数日或数月,以获取最后一笔收入的现实考量。
中国劳动趋势发布文章均欢迎转载!请记得说明来源,感谢!
如果你也对于数据新闻、实证资料或文献翻译有兴趣,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为理解当代中国劳动议题、工人处境贡献一份力!欢迎直接寄信到我们的邮箱: [email protected] 你可以在信件中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谈谈你熟悉的劳动议题或相关的实务经验。